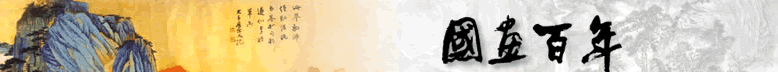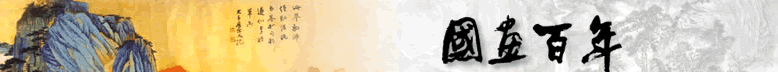寻找家园的伟大
--- 2O世纪中国山水画精神变革探索
对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评价,有过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形成于不同的时期,可见现实的价值判断和对历史背景的不同认识,都影响到了对山水画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山水画比人物画似乎更能反映时代在艺术家身上留下的烙印,因为很久以来,“山水”代表着传统的品格和精神,即便在196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强大到足以取代画家独立思想的时候,山水画中仍然或多或少地保持着艺术家的梦想,是无数受伤的心灵最后的乌有乡。因此回顾这段历史过程,我们首先采取的办法是:设身处地。
假设这是19OO年的一个黄昏,正是春色无限的好时节,一个画家信步出门抬头,满眼皆是“山水”。然而这“山水”已非昨日之家园,回到家来,冥思苦想,醒时梦中,这现实的真山真水又如何与我胸中之“山水”印证?“山水”的诗意又何在?
其实以上的假设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常常发生,不足为奇。但是,我们从中所要关注的是“时间”这个条件,生活在20世纪初年的山水画家是苦痛的,他们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无所适从:1、作为传统士大夫文化最大包容体的“朝廷"没有了,过去山水画家对于自然的赞美,有“在朝”的比照,因而愈彰显“在野”的价值,即使是完全的冲虚淡泊,在那样一个体制下,也仍然显得珍贵。如今,满目疮痍,继起的军阀混战,中外资本大行其是,铁路延伸之处,乡风骤变,几百年来诗意飞溢的山川风景之中,逐利之徒如过江之鲫。2、然而单此一种,还不足以动摇画家的内心,严重的问题是自变法维新以来的对于“体用”问题的讨论,到了民初,已酝酿成为一种势力强大的否定传统的潮流。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文中,对文人画极尽贬斥,他把近代画家的衰败归究于“写意"的滥觞,提出“以形神为主而不取写意,以着色界画为正而以墨笔粗简者为别派”。他的主张,得到了年轻的刘海粟、徐悲鸿等许多人的响应,更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陈独秀等人的在大的文化层面上的呼应,一时似乎形成对传统绘画的合围之势,白话诗的勃兴又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绘画的最有力的依托——古典诗词,山水画家的思想处境之艰难,由此可见。3、在清末民初传统绘画的世俗化潮流中,花鸟画、人物画的雅俗共赏的变革,在扬州画派、海上画派诸画家努力下,潜移默化着时代的审美之风,又有摄影术和西洋绘画的引进,因此,虽有许多有识之士,努力在革“四王”流弊中力倡宋元画风,但在大时势中显得苍白单薄,无力扭转社会对传统面貌山水画的看法。
从“我看山水”到“山水于我”到“山水之于大众”,中国画家遭遇了全面的困境。100年来,山水画家们还远离了“山水”,聚居于城市,他必然还要接受“城市”对于他的眼睛和心灵的异化,这种“异化”最大的因素,便是“工业化”对社会的影响,由此引起与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撞碰。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在20世纪坚守传统,并卓然有成的山水画家无异于生活在“异乡”之中,他们在“异乡”中描绘理想的故乡,其精神放逐意义,已超出了绘画的本身,而具有思想的价值。好在许多许多的山河依旧,现代交通条件为现代画家出游也提供了方便,又有些画家在颠沛流离中不无痛苦地亲近着山河。20世纪后半叶,更有许多画家主动到大自然中寻求画材,“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古训获得了新的内涵。中国人依然在内心深处喜爱山水,这为山水画的延续与新变提供了最广范的社会基础。
二
在最初的重要人物中,我们也许要反复提到两位英年早逝的画家——金城和陈师曾。1914年,中国最早的国家博物馆——内务部古物陈列所在故宫展出历代书画,使当时只知“四王"的人们对中国绘画史有了更多的理解,这件事,金城是其功不可没者。1920年春,金城与周肇祥、陈师曾等人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虽以临摹为主,但由于他尊崇宋元山水画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对扭转了“四王”的颓风影响深远,扩大了传统承继的视野,为后来的山水画的变革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其弟子中,有相当数量成为后来独树一帜的有影响的画家,如秦仲文、胡佩衡、吴镜汀、陈少梅等等。金城的对宋元的重视还促进了对“南北宗"看法的综合,而北宗的注重对象较为写实的描绘,呼应了新文化运动对于现实的主张,甚至与康有为的思想不谋而合,“若夫传神阿堵象形之迫肖云尔,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即可记形也,
遍览百国作画皆同,故今欧美之画与六朝唐宋之法同”。(康有为语,出处同上)陈师曾是位天才画家,他家学渊源,且有留学经历。他于诗、书、画皆有过人才情,且熟悉画史。他的山水受石骼、石涛、龚贤、沈周等人的影响,用笔意气纵横,率意中显出从容与自信,在当时“四王”画风泛滥时尤为引人瞩目,产生过“振衰起溺、补偏救弊’’之功;他的近于写生的一些园林小品,有时甚至融入了西画技法,而又恰到好处;他对齐白石的艺术影响已被传为佳话,其意义自不是一般意义的提携,而是在思想上对齐白石的指引。齐白石的变法意识实际上是人的自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高扬,他的前期山水显然已远离“四王"体系,而具有耐人寻味的创造性诗情。
三
民初从画界内部对“四王”的山水画僵化的否定,足可认为当时的传统画界的种种变化,也已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社会巨大变革面前,传统画界试图以自己的角度,来诠释对传统承继的见解,因此,与文学中的对国故派不能简单看待一样,画界的这一种倾向,也自有他的进步意义。如果没这个共识,我们也就无法将要提到第三位重要人物——黄宾虹。
在20世纪1OO年传统绘画发展中,黄宾虹是一位评价差异出入甚大的人物,他生前比起齐白石、林风眠、潘天寿等人来说是寂寞的。但是在近10余年间,尤其在世纪末中国画学界的一次又一次对他充满敬意的注视,却表明黄宾虹的艺术还未被完全认识,而有着超越时代的价值。
黄宾虹的意义在于对“笔墨”问题的“精神”提升。长时间以来,传统画家在形式上的陈陈相因,成为一个诟病最大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历程中,激进反传统主义大多处在主流地位。如五四时期,抗战初期,50年代至80年代。在不同时期,他们的表现形式、理论言谈与行动口号不尽一样,先后有“中国画落后”“中国画不能为抗战服务”“中国画不科学”“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中国画是封建主义”“中国画没有现代性,不能走向世界”“笔墨等于零”等等。但本质没有大变化,都否定或基本否定中国画的价值与意义”(郎绍君《笔墨问题答客问》)。但是随着对黄宾虹认识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当年这样片面的否定是粗暴和可笑的。在革命的年代,黄宾虹从一个反清的民主革命活动战士,在辛亥革命成功后,谢绝仕途,而尽快转向他认为可以救国的学术研究,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他这种想法与此后长期的水墨山水的实践,比稍后的蔡元培提出的“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从中国美术史的发展意义上说,要深远得多。归纳起来谈,黄宾虹在近世的山水画发展上,解决了以下的重要问题:
1、传统的山水画其基础仍是国学,儒家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一,而道家的自然与人融为一体的观念,更是传统山水画学的精神源泉,然而此时国学受到诘难,山水画的基础何以建立?黄宾虹选择了“学问”,他的“学问”是对国学的重新反思,而非如当时激进西化人士那样全盘否定国学。黄宾虹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人心舆论的关系上,深切感到“著书立说,申明主义”的重要性,所以他认为“今之急务,又不存乎言论,而在乎真实的学问”(黄宾虹语,《大学汇刊》发刊词,1912年6月),因而黄宾虹弃政从学,一心学问,甚至与友人组织“国学保存会”。通过这种不合时俗的潜心学术,黄宾虹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飞跃到一个新层次,他得出了“欧风东渐,心理上契合,不出廿年,画当无中西之分,其精神同也”(出处同上)的结论。现在看来,黄宾虹对中西绘画精神相同的判断,就20世纪后来的中国优秀山水画家的实践看来,是极具有前瞻性的论断,尽管证明的时间长了一些。对国学的反思是20世纪中国山水画新的一个出发点,它摒弃了人们对于五四以来的绘画徒具僵化形式而无深刻内容的偏见,使艺术重新回到正大的道路上来。
2、但是单谈“精神"是不够的,此“精神”如何与艺术直接关联?画家如何通过绘画形式体现这种“精神"?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黄宾虹提出了著名的、影响深远的“笔墨”问题,他声言,“笔墨”不是仅为“形式”,笔墨精神即为中国艺术精神之所在。黄宾虹说“鄙意以为画家千古以业,画目常变,而精神不变。因即平时搜集元、明人真迹,悟得笔墨精神。中国画法,完全从书法文字而来,非江湖朝市俗客所可貌似。鄙人研究数10年,宜与人观览;至毁誉可由人。而操守自坚,不入歧途,斯可为画事精神,留一曙光也”(《黄宾虹传记年谱合编》)。这段话与黄宾虹关于学问的思想结合起来看,就可看出
“笔墨”问题在他艺术思想核心中是操守、是人格、是精神,而绝非单纯的技巧。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关“笔墨”问题的大讨论,反对者和肯定者都忽略了“笔墨”背后的人以及人的精神这个大条件,而我们现在看黄宾虹的“笔墨”论及其他的山水画实践,也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理解在激荡背景下革新中国画的真正目的。
黄宾虹在创作上探讨了“笔墨”与山水的关系:“以山水作字,而以字作画。……凡画山,不必真似山,凡画水,不必真似水,欲其察而可识,视而可见也;故吾以六书指事之法行之。”(《黄宾虹传记年谱合编》)与吴昌硕的以金石入画不同,黄宾虹强调的是“六书指事之法”,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独“指事”与绘画有特殊性,用今天的话来讲,“指事”含有某种意义上的象征性。笔墨的“象征性”问题在黄宾虹的山水画中有一个发展过程,他的五字笔法、七字墨法,最后归结到“点”上,尤其是晚年,几乎无“点”不成画。他通过“点”不但解决了“笔”与“墨”的矛盾,而且在整个画面的点的经营中,使“笔墨”特立独行,通过象征性强化到精神的层次。今天看来,黄宾虹的山水题材布局构图不见得有多新,但由笔墨而来的“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尤其是晚年因目力不逮,所画已近抽象的山水作品,更说明了“笔墨”的那种精神的力量。
因而黄宾虹也好,稍后的潘天寿也好、张大千也好,后世的美术史家在将他们仍归入传统派,并表示局限的惋惜,同时又不能不说,在20世纪中,这几位传统派的大师对中国画成就最大,贡献最多。
在20世纪前期,传统派的山水画家应该说是仍然占据着画坛主流。如北方的姜筠、贺良朴、姚茫父、溥心畲、萧俊贤、萧逊、祁昆、陈半丁、胡佩衡、刘子久、秦仲文、惠孝同、吴镜汀、陈少梅、关友声、黑伯龙等;南方的陆恢、吴观岱、顾麟士、吴徵、冯超然、吴子深、张大千、吴湖帆、汪采白、汪铎、贺天健、郑午昌、顾坤伯等;广东则有赵浩云、卢振寰、卢子枢、黄君璧、黄般若等……在中国画的变革潮流中,他们也各依古法逐步地探寻出自己的风神。
四
美术史家朗绍君在对20世纪中国画坛诸流派作了如下分类:1、传统型: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李可染、傅抱石等等;2、泛传统型:高剑父、高奇峰、徐悲鸿、蒋兆和_、林风眠、吴冠中的水墨等等;3、非传统型:林风眠、吴冠中的彩墨,赵无极、朱德群的抽象水墨,以及现代的“实验水墨”。朗绍君的这个分类法,不仅对整个中国画,而且对于山水画来说,也是基本适合的。整个20世纪,山水画取得杰出成就者,仍是传统型和泛传统型的艺术家,虽然他们从中国山水画整个历史来看,这100年只是前进了一小步,但是其中却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严格说来,齐、黄、潘、张等人都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前面说过,山水本身的意义以及受众看山水的态度都变了,而同时又有西化风潮之迫,传统受抑,又兼有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因此在这样背景下山水诸大家的发展,使得山水画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象征,他们在一个特殊的场景中,保存并延续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根。也因这一点,在20世纪末的时候,黄宾虹、潘天寿、李可染等人益显伟大。当然朗绍君的“泛传统型”的分类和界定都显得过于宽泛,这里面的林风眠、徐悲鸿两人的艺术道路,是应该区别对待的。实际上吴庆云、高剑父、陶冷月等程度不同地参用西画光、色、气氛的渲染,都是想创造一种折衷古今中外的新途,只不过艺术格调尚未进入更高的艺术层次罢了。
林风眠在山水画上的贡献,似乎不能用一句中西结合的话来概括。中西结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除了学理上的理解,更主要的是如何寻找一条具体的可操作的道路进入到画境中去。林风眠不用说有极深的西画修养,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一九三五年的世界艺术》可说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现代艺术流派的著作之一。然而如何在中国的情境中走一条有特色的路,远比学理上的议论来的艰难。在林风眠看来,决定中国绘画的是一些本质性的东西,而非程式和笔墨。他在汉唐艺术那里找到了源头,并抽离出“线”这个要素,但此时的“线”并非孤立的,林风眠指的是连接“汉唐”精神的线。与黄宾虹的“精神”性山水相反,林风眠选择了“情感”表现,他从自然中感受那些他所亲近的山水风物,凭记忆和技术经验去作画。他在“笔墨”上与吴昌硕恰恰相反,也有别于黄宾虹,他反对书法入画,“书法和绘画究竟是不同的东西”(林风眠《中国绘画新论》1929年),也坚持不在画中题诗,为的是不让诗破坏绘画的独立性。他对颜色有着自己的理解,大胆地将丰富绚烂,但又并非纯自然的物象之色,引入到绘画里来。可以说,以上种种都是与传统诸大家的承继南宗文人画传统背道而驰的。但是林风眠却成功了,他的成功在于在新的世纪里,真正改造了似乎是不可改造的势力强大的传统绘画。我们今天面对着他的《江上》、《沿江村落》等作品,任何一个只要不抱偏见的人都能从中感到突破传统桎梏的鼓舞。这种追求,实际上也是传统型诸大家所希望的。齐白石花鸟、山水画的俗化,并非艺术家真的摆脱不了匠气,而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俗中见雅”,但是由于西画学的修养,齐白石不可能走到林风眠这一步;黄宾虹的晚年几近于抽象的点以及焦墨,实际上也是一种突破传统之策,然而他只是从传统的内部将这种革命推到极至,而不可能如林风眠这样与文人画的彻底决绝,但是三人却都在最后殊途同归。可以说,20世纪中国山水画,如果没有林风眠的出现,是遗憾的,而黄宾虹的独自意义,也会因没有林风眠而大大削弱其光彩。
五
还需要重视的是20世纪后50年的山水画家们。前面之所以说“泛传统型”的分法分得过于宽泛,还在于这个年代的一些杰出艺术家,虽然在他们的晚年,其作品风格大致确可归入泛传统型,然而这一些人的心路历程、生活方式等等,却和传统型诸大家有许多不同。徐悲鸿写实主义的提倡,决不是留学者的食洋不化,也非政治的投机,而是他坚信科学的重要,由此引伸出客观、正确描摹现实对于改造中国艺术的重要。徐悲鸿的这种思想与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旧文化的批判,对于当时先进阶层对德先生、赛先生的欢迎是一脉相承的。徐悲鸿在中国山水画创作上也与油画一样言行一致,他画的松林、人物,其枝干生长,人物与景的比例,基本上是西画的方法,但是却也画得清新刚健,笔墨韵味十足。50年代的李可染、张仃、罗铭,以及江苏画派的傅抱石、钱松喦等人,长安画派的赵望云、方济众、石鲁等人和岭南画派关山月、黎雄才等人的重视写生的山水画的变革,应该说是时代的文化价值观的使然,而非徐悲鸿的影响。写生并非此时独创,浙派诸人早已尝试,然而以水墨的手段,如西画般入手去写生,所得的山水面貌确与传统迥异,他们的山水画风在五六十年代的转变,不能一概归究为政治因素,而实在也有改变传统国画的决心和考虑。他们是承先启后的人物,没有他们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承继,便没有90年代的实验水墨等新兴的国画变革思潮。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应该说是变革幅度最大的时期。老一辈画家中陆俨少、张仃等人可谓传统派的变革者,朱屺瞻、刘海粟等人浓墨重彩的表现已颇具新意,而吴冠中和周韶华是可以称作实验水墨的新派。更有一大批中青年家或探寻传统之根,或借镜西画构成,他们在“造化”和“心源”之间正在苦苦寻找着各自的“家园”,对于他们的未来,史论界正有所期待。
六
如上所说,20世纪中国山水画家所面对的痛苦和无所适从,是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工业文明的日新月异使传统山水景观不复存在,追求精神理想的艺术家的内心失落是空前的;然而最重要的还不仅仅是景观,与山水画家息息相关的痛苦,是传统文化及其由此而来的价值观的动摇,或破灭,或冲击,使他们真正无法在内心里找到“家园”。没有“家园”也就谈不上“在”家园,更遑论家园“表现”?因此,我们反过来可以从20世纪山水画的发展中看到一部无数画家寻找理想家园的可歌可泣的伟大历史。
2001年12月5日于北京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系主任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