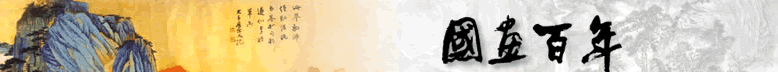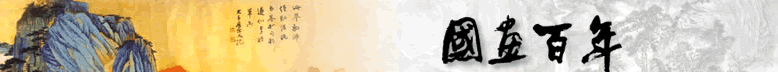桃花依旧笑春风
--关于中国现代的花鸟画
刘曦林
一
“现代”,在这里作为一个时代概念,大体和刚刚过去的20世纪相合。尽管现代中国花鸟一类绘画艺术有着鲜明的现时代特色,但毕竟不是最摩登,因此“现代”在本文中并非等同于现代主义(Modernism),而只是谈到风格、语体时含有时新之意。
二
关于花鸟画的界域,在现代似乎有些太宽泛了。
花卉、翎毛、畜兽、草虫、蔬果、龙鱼和“四君子”画,甚至在题材与格局上类似西方静物画和动物画的水墨或彩墨表现也归入了此科。因此,我曾经认为:“我们今天所谓的花鸟画学,是以植物、动物形象及其相关物为题材,藉以表现人,表现人与自然、与造化、与社会关系的诗化了的造型学问。”
三
现代中国的花鸟画是在承传并变革古代花鸟画的矛盾运动中生发的。从承传的一面讲,它不仅仅是对清末技法、样相的简单延续,而是继承了整个古代中国画、古代花鸟画的美学传统。
明清二季,文人花鸟画成为主潮,院体画、工丽派走向式微。文人画重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弱化了造型的写实性、精微性及色彩的丰富性,强化了艺术的主观性、表现性、抽象性、书写性、随机性,强化了文思和多样艺术的综合性,强化了水墨语汇的纯正性,使花鸟画艺术发生了重大突破。20世纪的花鸟画所面临的正是这种总体的情势。从就近的传统而言,20世纪的花鸟画更多地受到了18、19世纪画风的直接启示,并受到20世纪大文化背景的促迫,在美学品格上发生了诸多变异。
四
画家们大都期望无为地自自然然地生息,然而艺术并不生存在真空里,花鸟画作为文化子系统的一个细科时时受到大文化背景的影响。
在这个世纪里,给予艺术以重大影响的首先是政治的变革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的革命,另一社会文化因素是西学的冲击。西潮不仅使整个中国美术形成了中西美术并存的格局,也为中国画融合西画的新派创造了机遇。由于写实主义的提倡,使重视物性、物理的宋代院体画展现了隔代复兴的希望。这种情势使文人花鸟画受到压抑,也间接地受到促动。西学的冲击只是使中国画坛丰富了营养,丰富了品类,使花鸟画多了一条融合西法的渠道,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和审美基础的花鸟画并没有被全盘西化论摧垮,却在“物竞天择”中显示出不已的生命力。传统的中国中心论已被现实打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只会刺激东方文化的自强信念。经过一个世纪的反省,我们悟到了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可贵,也悟到了开放的全球意识的必要,中国花鸟画将在创造性转换中寻求其现代品格。中国花鸟画的这种创造性拓展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需要,也是以其独特性丰富世界文化之需要。
五
由于上述社会革命的促迫和持续不断的西风劲吹,使变法、变革、图治、维新或者说传统与创新的矛盾成为整个世纪的潮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好,“西学为体,洋为中用”也好,变化出一个新的艺术世界来又是所有不安于现状的画家的愿望,于是形成了古今中外的艺术现象齐集一堂,各种变化途径争奇斗胜的局面。从语体的角度看,2世纪的花鸟画坛已非徐黄异体或疏密二体或院画与文入画的简单延续,而是简笔、半工半简、工笔三种传统语体的创造性转换与融合西画的新体共存的新格局。
1、简笔语体与文人画的转换
虽然陈师曾维护文人画的立场有特殊的意义,但文人画作为思潮性的流派已成为历史,但作为一种审美样式及其文人传统并不会顿时消亡,文人画惯用的简笔水墨语体也可以作为一种形式在传达新的情思中继续充实和演化,而在时代的变革中找到这种审美样式与时代精神的中介使其稳妥地发生转换,正是中国人、中国哲学的“中庸”式的变革选择。文人画时代的结束和文人画在转换中获得新生,这仿佛是一个悖论,但又最明晰地彰示了传统艺术在承传和变异的矛盾中前行的规律。从文入画语言自身的变革来看,它仿佛在清朝末年还没有走完本体的历程,从包世臣到康有为崇碑轻帖的书法美学思想对画学的影响,浓烈的色彩与墨色交互辉映所产生的新的视觉程式在“前海派”那里刚刚开始展现出曙光而有待拓展。正是融入北碑笔力、笔意的进一步文人化和墨色情趣进一步市俗化这种似乎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化合,为20世纪文人简笔花鸟画的转换奠定了基础。
凌跨19、20世纪被称作“后海派”领袖的吴昌硕,承续着“前海派”的美学思想,进一步以篆籀之力、金石之气入画,适应城市平民文化情趣,更取西洋红等明亮色彩,进一步改变着以水墨为上的文人画观念,改变着以淡色为宜,认为“作画以深色最难”,“写意而设色者尤难能”的文人画成见,是本世纪转换文人简笔画风的第一位代表人物;齐白石除着意于诗、书、画、印的全面修养之外,又依着他那农民的本色,把乡间的自然情趣和思乡情结,把民间艺术的造型、色彩融入文人画笔墨之中,洋溢着一颗童心和农民的朴实的审美意识,是转换文人简笔花鸟画风的第二位代表人物;潘天寿把时代崇尚的健康向上的精神,以阳刚之笔、崇高之境、奇崛构成巧妙地与自己的人格力量熔为一炉,并把墨戏作风转换为严谨的经营,类似学院派的作风或学者般的风范,使简笔花鸟画成为一门严肃的学问,是简笔花鸟画朝现代转换的第三位代表人物。这三位大师和王一亭、陈师曾、李苦禅、朱屺瞻、崔子范及中年画家张立辰等集结为一个强大的简笔花鸟画流派,书写了20世纪花鸟画史最辉煌的一章。虽然他们程度不同地保留了古代文人孤高清寂的品格,但从总体上使简笔文人花鸟画风发生了由士人向民众、向现代知识分子,由隐逸向入世,由阴柔向阳刚,由淡雅向浓烈,由古代形态向中国画自身的现代形态的转换。
与人生的切近,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丑恶的反抗,于理想的热情,于自由的向往,阳刚的力度,浓艳的色彩……成为文入画的转换者内在的美学愿望,但并不是所有的筒笔画家都有这样的追求,简笔使笔法及其内涵经受着格外严峻的考验,简而空泛、率而无意是简笔一路最大的危险,以为笔简即是“写意”更是美学上的误会。
2、半工半简语体及其避俗的努力
俗称“半工半写”、“兼工带写”或又称作“小写意”的花鸟画语体,由于兼顾到物态、物形、物色、物性的写实性和笔、墨、色的生动性,兼顾到文人意趣、个性、才学与欣赏者普遍接受的可能性,在美学情趣和工致程度上介于简笔、工笔之间。它和简笔语体并无严格的分界,只是笔法和主观性程度的差异,如果说花鸟画是现实与浪漫的结合,主观与客观表现的统一,简笔一路更倾向于浪漫主义,是浪漫中的现实,有自我背后的共性;半工半简一路更倾向于现实,是现实中的浪漫,有共性中的自我。
从半工半简体语就近的传统来讲,除了17世纪的恽寿平、18世纪的华喦之外,上承陈洪绶的三任(任熊、任薰、任颐)尤其任伯年以鲜活生动的造型和明丽可人的色彩成为20世纪画家效法的宗师。如果说这一语体从任伯年到本世纪上半叶,有过倾向于文人的反抗或高逸情趣和倾向于市俗、市场欢迎的幽雅之美两种倾向的话,在50年代之后则倾向于社会所提倡的健康、美好的共性的审美情趣的表现,艺术家的自我几乎完全服从了社会,只在形式上流露着较多的个性风采,当然,这也同时是整个艺术遇到的问题。
半工半简语体在造型上不走极端,既乏简笔因夸张带来的力度也避免了简笔容易产生的粗率和空泛,不如工笔那样精谨也避免了流于匠气、拘于形似的风险。它以笔墨的丰富性、表现生物的鲜活性和色彩的润泽明丽见长,以表现轻音乐般的幽雅精致为美学特色,基本上属于优美型的艺术,或者说具有“形神兼备”、“雅俗共赏”的可能性。我以为“形神兼备”和“雅俗共赏”都不是十分严谨的说法。正如简笔同样有形,工笔同样传神那样,简笔也有极俗,工笔也可极雅。雅与俗如果指审美主体,实难以共赏,如果指美学品位,更不应混同。雅俗不在于题材,不在于语体,也不在于优美或壮美,不在于为士大夫服务还为大众服务,而在于艺术的修养和文思。因此,半工半简语体的画家恰恰最易为此所误,不是尾随了市场,就是尾随了较为浅层的审美趣味,比较突出地存在着“媚俗”问题。
但20世纪的半工半简花鸟画依然有不凡的成绩。重写生,重笔墨,重修养,重文思,重个性,是这一流派中成功的艺术家抵御媚俗的有力手段。王梦白兼学吴昌硕,强化了这一语体的力度和量感,是本世纪前半叶的重要画家;王梦白的弟子王雪涛,造物生动,技法熟练,前期雅逸,后期偏于艳丽;江寒汀兼学虚谷、任伯年,尤其虚谷笔法的参用有益于这语体格调的升华;郭味蕖修养深湛,在生活中每创新境,在努力适应共性审美需求的情势下成为五六十年代创新的榜样;于希宁专攻花卉,注重文思和诗情,晚年以“才德勤修养,三魂(国魂、画魂、人魂)共一心”为座右铭写梅,是新时期的代表;中年画家中,王晋元、郭怡琮等是拓展这一语体的主力。
3、工笔语体的复苏与写实主义
世纪之初,康有为主张“以院体为画正法”,“以复古为更新”,又主张“以郎世宁为太祖”,“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鲁迅也认为,“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遂主张“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因之,对文人画的批判,对宋代院体的重新发现,倡导写实主义便成为顺理成章的思路,使工笔花鸟画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旁落之后于20世纪获得新的机遇,于是也有了几位工笔花鸟画的大家。世纪初,高剑父、高奇峰上承居廉、居巢,借鉴日本画风,欲图创立“新宋院体”,对气氛和质感的表现尤其重视;于非闇最崇赵佶,以瘦金书入画,作工笔重彩花鸟,前期工而近雅,后期端庄富丽.有弟子田世光、俞致贞等继其业;刘奎龄上承郎世宁,借鉴西法塑鸟兽之形,远较郎氏松活;陈之佛参融工艺构成入画,前期有雅逸之佛性,后期多明丽之心;陈子奋工篆刻,尚白描,以金石之力为笔意,别具一格。他们分别为复兴工笔画作出了贡献,成为“文革”前工笔花鸟创新的代表。新时期,由于整个工笔画坛的集结意识,工笔花鸟画家的队伍空前壮大,思想也远较前人开阔,李魁正、周彦生、冯大中、江宏伟、林若熹等一大批新手崛起,或重于光色的整体效果,或赋予动物以人性的表现,或再造宋画古穆神韵,或新创现代构成之格,使工笔花鸟画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现代样相。
从美学思想的层面上讲,有文思的工笔画家并没有简单地复制古法古意,他们意识到“写意”和浪漫、想像这些美学概念并不独为简体所有,工致的笔法与纯化的色调,简明的构成,象外之意综合的表现,完全可以升华工笔画的美学品格。但过分靠近日本画的气氛渲染和装饰、厚涂处理,或者迷于添加剂产生的肌理,或者又受到超级写实主义在市场效益上的诱惑不厌其烦地制作,不知恰到好处,则有可能使之趋于匠气,而弱化了中国笔墨的表现性和独有的格调。它同半工半简语体一样地遇到了“雅俗共赏”的难题。要害仍在是否有文思,不仅工于形、工于笔,还要工于意,工于意外之意。
4、融合中西的新体与西方美学
融合中西的新体,是在中西绘画并存互补的格局下出现的新潮样相。这一新体的出现和传统中国画尤其文入画的历史性转折,是20世纪花鸟画演化的两大特征。但由于采融西画的渠道和角度不同,以高剑父、徐悲鸿、林风眠领衔又有三个支脉,与传统三体共同构成两大体系,“三三格局”。
高剑父、高奇峰等留学日本,采融了曰本圆山四条派和朦胧体对形体塑造和对光色、气候、气氛的渲染法,表面上是“中日混合派”,但因为这种新的日本画风是西洋画风渗透于水墨画的结果,而归根到底是对写实西画的融合,后人称之为岭南画派。但写实西画的真切感弱化了中国画笔线的骨力,填塞了传统中国画空白的余韵,在当年褒贬不一。陈树人较为特别,他仍以半工半简的传统笔法处理折枝结构,却强化了同向线型结构的节奏感,有西画构成意味。岭南派的第二代传人中,关山月、赵少昂、杨善深均能作花鸟画,以关山月为代表发生了回归传统笔墨的变化。
徐悲鸿对古代花鸟画评价最高,因保有写实精神为多,故认为“造诣确为古今世界第一位者,首推花鸟”,“画中最美之品为花鸟”,花鸟画是“世界艺术园地里,一株特别甜美的果树”。所以,他主张“以写实主义为出发点”,以“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复兴中国画和中国花鸟画。由于他对西画塑形技巧和解剖、透视学的精深把握,对“写实”与“写意”取辩证观,以西画体面关系与中国画笔墨相化合描绘马、狮等走兽成绩最佳,在情思和艺术表现层面上已远过郎世宁和岭南画派。徐悲鸿将素描的形体观念与花鸟画笔墨相化合,犹如蒋兆和化素描于人物画,李可染化素描于山水画的成就,同时赖于他们分别对中西画研究的深度。如果他们于素描、于笔墨都是俗手,将无以与传统派的变革者相抗衡。
如果说徐悲鸿属中体西用,林风眠则有中体西用的水墨花鸟和西体中用的彩墨静物两种样式。其彩墨静物,取西方静物画之构成,是西方现代派的早期表现移植于中国画坛的果子,较之其水墨花鸟一格更倾向于西画体系。他的新贡献是真正将西画的色彩观念引渡到宣纸上来,创立了一种新的形式。
以上融合西画的诸种新体,程度不同地疏离文人花鸟画传统,弱化了书法笔意,是20世纪画坛上最勇敢的创造者,然而总体成就并未超过吴、齐、潘等传统文人画自身体系的变革者群,也许他们还需要时间,况且中西美术也不可能有什么严丝合缝的综合。
由于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提倡,五六十年代的花鸟画坛并没有出现融合西法的新的代表人物,徐派弟子刘勃舒的马反而弱化了素描痕迹。世纪后期的中青年画家们更倾向于在传统中国画的笔墨构成和西方表现派、立体派、抽象派的造型、构成意识之间寻求沟通的可能性,舒传熹、张广、姜宝林、张桂铭、陈家泠等人正致力于使花鸟画进一步趋向现代形态的试探,是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新体。其前途不在于去忙着打倒其他语体,而在于自身体系的完善。潘天寿在论及东西绘画互相吸收时说:“必须加以研究和试验。否则非但不能增加两峰的高度和阔度,反而可能减去自己的高阔,将两峰拉平,失去了各自的独特风格。”这也许是所有致力于融合西法的实验者承担的最大风险。
前述各种传统变革语体和各种新体至今仍活跃在花鸟画坛上,也许时代的进步正表现于各语体的共处,避免了各种美术革命时期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至于各语体的生命力将不在表面的新旧,而在自身语言规律的把握,自身语言精深的程度,以及这语言所承荷的内美、文思、情趣的深浅多寡。
六
花鸟画家的内美及主客观意识,不仅在于人与社会的关系,还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是否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关系,后者更具花鸟画艺术的特殊性。梁启超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这确与“三界惟心”的佛教思想一脉相承。但从他下文所举的有关花鸟诗句来看:“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与“杜宇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同一黄昏也,而一为欢憨,一为愁惨,其境绝异。“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同一桃花也,而一为清净,一为爱恋,其境绝异……他的结论虽是“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的唯心学说,但却道出了百、千、亿人感触同一自然必有百、千、亿种“乃至无量数”心境的艺术哲理。在共性意识压倒一切的文化环境里,花鸟画家缺少的正是这种人各为一的心。等而下之者,受那美是客观说的影响,只着意那客观存在的自然美,唯物主义的原则是未曾违背,失去的却是美的灵魂。我倾心于主客观统一说,更主张由形而下升至形而上,这恐怕是花鸟画避俗的最紧要处。
苏东坡言“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与郑板桥所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与白居易所吟“花非花,雾非雾”,与陆放翁所谓“一树梅花一放翁”同理,都是主客观同一,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伟大胸怀在中国诗歌、中国花鸟艺术中的体现。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当今世界,日益显示出大自然的可贵,亲和万物的可贵,纯正的无利欲的自然观和艺术观的可贵,美学意义上的“自然者可为上品之上”的可贵。世界化、一体化化不了中华民族对花鸟艺术的痴情,现代化代替不了手绘的卷轴画,在那素洁的宣纸上,在人们审美的心灵里,千秋万代悄然过,桃花依旧笑春风。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注:
①刘曦林《二十世纪花鸟画概说》,《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画3.花鸟(上)》,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6月版。
②前人、今人曾将“写意”、“大写意”作为与工笔画对应的语体概念来使用,实不确。“写意”为美学概念,工笔画亦有写意意识。故将通常所谓“写意”流宗称为“简笔”。参看笔者《向现代形态转换的求索一’89后的中国画》一文注②.载《文艺研究》1994年第4期。
③《万木草堂藏画目》,上海长兴书局戊午二月(1918年)印行。
④《且介亭杂文末编·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⑤《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⑥徐悲鸿引文均见台湾艺术家出版社出版《徐悲鸿艺术文集》。
⑦《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转引自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潘天寿谈艺录》第21页。
⑧《自由书·唯心》,载《饮冰室专集》卷二。转引自中华书局1981年版《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以 下梁启超引文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