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周婉京:“好上加好”的艺术圈,为何成为平庸的制造机?
时间:2020/11/19 9:31:38 来源:Hi艺术
文 | 周婉京
编辑 | Jade
图片提供丨周婉京、本刊资料室
本栏目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周婉京
作家、艺术评论人
资本的原始累积往往伴随着罪恶。这期的专栏,我想从这句话开始进入,审视一下“艺术家算法”“藏家维护”和“不做知识生产的展览”这三种跟“罪恶”可以相关但不必要相关的领域。然而这三个“罪恶”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本上都发生在疫情之后重新活络的中国艺术界生态之中。 那些疫情之前留下的制度问题似乎并未得到解决,便又以新的更庞大的形态卷土重来了。
这个月在上海与南京出现的一些展览,用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形容便是“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紧跟一只大灰狼” 【1】
,多数是直观的,观念和信息都一目了然,甚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根本无需耗费过多精力和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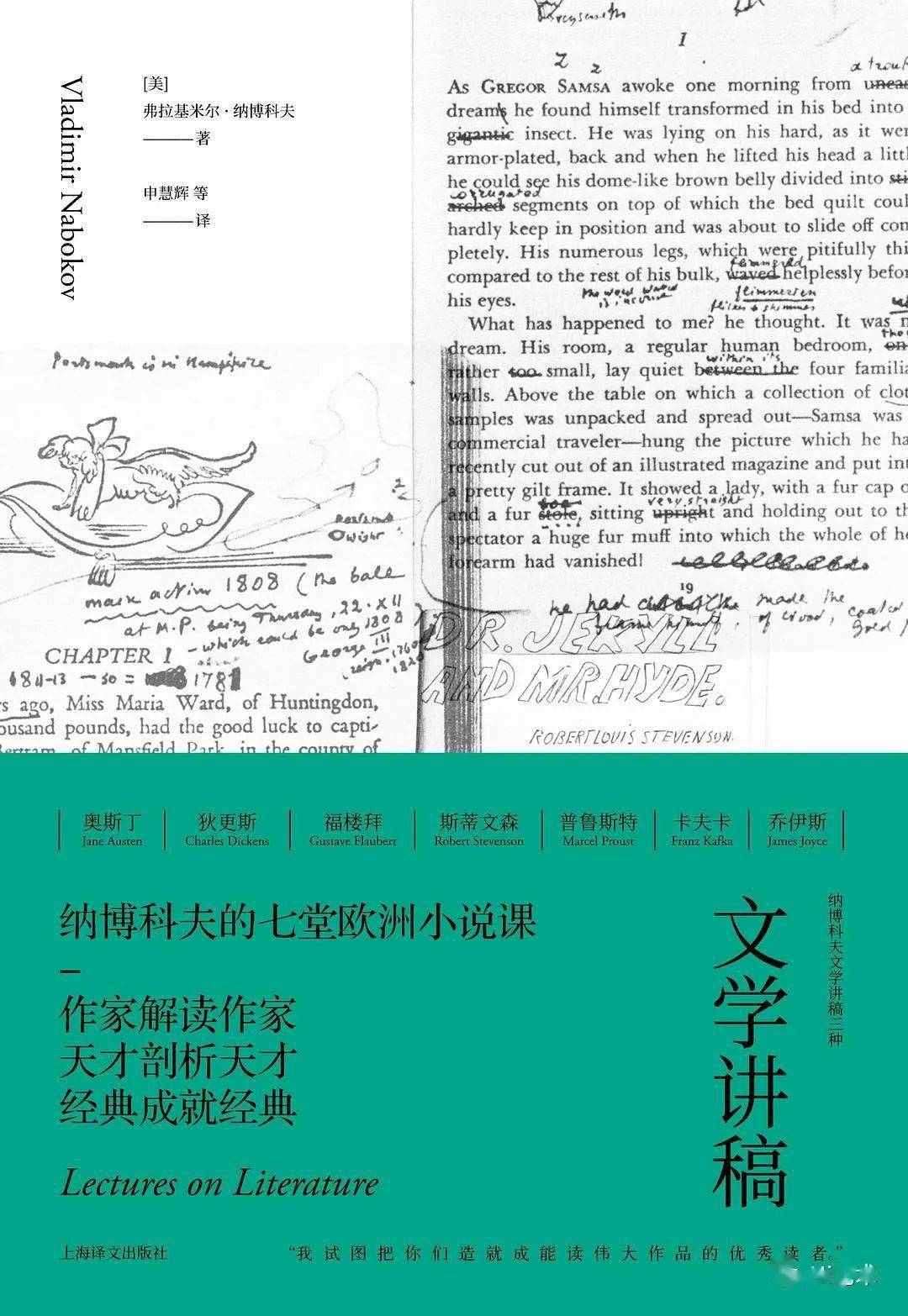
以纳博科夫1950年代在康奈尔大学讲授欧洲文学的讲稿为基础整理而成的 《文学讲稿》
这些展览中没有时间与空间的调度,策展人的思想和艺术家的旧作,无不例外地授引自常识的古已有之的老概念。平庸正在以倍数递增的方式贩卖自己,以至于一个原本可以做出好作品的艺术家也在这样生产平庸的语境中成为了平庸的帮凶,所做的都只是粉饰平凡的事物。这些人不去操心艺术可能具有的任何创造性,而只想从旧家当、老故事里面找出几件得用的家伙来炮制作品,如此而已。后半句同样是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用来批判平庸作家的。 【2】




上海艺术周期间的某个活动上,一个由上海的公共艺术专业的学生组织的行为表演现场,每个人的身上都贴着硕大的“平庸”二字
“艺术家算法”的失落
也许你会觉得既为“平庸”,那么也就没什么好唏嘘的。而真正令人唏嘘感慨的是,一些原本擅长做一些小品类摄影、处理私人记忆类问题的年轻艺术家,忽然在今年(疫情以及一些国际驻留之后)决定转而做其并不熟悉的装置。新作不仅暴露出艺术家对装置类作品缺乏认知,而且将自己并不丰满的感知体系暴露在众人面前。那展览的样子就像一条水鱼搁浅在沙滩上。
这种转型的失败,我想称它是“艺术家算法”的失落。在我最近看过的上海一家本地画廊的个展中,一个做此类“算法”的艺术家便用很大的词来概括她自己的作品。非常有意思的是,她想要表达的恰恰是微小的、隐痛的现代人的情感。可是当她用大词来描述小情时,不但大词不再好用,作品本身也成为颇为类似的一种景观。
不是说景观一定不好。相比之下,当前正在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展出的克劳蒂亚?孔德(Claudia Comte)的《死亡之舞》(La Danse Macabre)就要好得多。虽然孔德呈现的也是景观,有着记录大型户外雕塑被火焚烧的场景,还有对更深一层——从14世纪欧洲鼠疫到2020新冠病毒的现实景观的重新想象。

"80后瑞士艺术家"克劳蒂亚·孔德的《死亡之舞》,影片截图 图片致谢:上海油罐艺术中心
这里也不是说景观就一定要具有饱满的现实感,神秘同样可以成为景观,但不应该是以软弱无力的视觉修辞格的方式。这个视觉修辞语言的问题在近两年来充斥着中国当代艺术圈,几乎成为了一种高度形式化却又最容易成功的“神秘”捷径。这种诗意往往会给观众的观看带来一种喜悦,具体而言是一种兜兜转转看完了整场展览却仍没看懂任何内容,这时忽然从墙面或地面上发现某行自己读得懂的诗句时的那种狂喜。这种喜悦并非与展览本身有关,而是拾得性解读带给人的“救命稻草”感——一种由“我终于看懂了这个展览”带来的短暂的自我满足。

克劳蒂亚·孔德 《哈哈哈》 600×4000×40cm
18个杉树树干 2014
摄影:Gunnar Meier 图片致谢:
上海油罐艺术中心


克劳蒂亚·孔德 《是否》 600 ×2000 ×50cm
每个字 松树各由两条船拉 2016
摄影:Gunnar Meier
图片致谢:
上海油罐艺术中心
“藏家维护”:维护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展览让我联想到近几年充斥在艺术圈里的以拼贴、挪用和转译为表现手法的一些作品,其指涉的内容大多数与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有关,注重报纸与宣传媒介上露出的各类信息。
有趣的是,虽然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摆出了一个批判的姿态,却在本质上顺从着其所批判的意识形态,试图成为新的集中式权力的代言人。这类的艺术家通常特别能说会道,可谓“博闻强识”。他们在使用这些意识形态语言的同时,也扮演了“全系统”的角色,身兼创作者、批评家、策展人等诸多身份。
一般人将这种跨圈的情况形容为“斜杠”,一些读过或者听说过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人把这些跨圈现象称作为“块茎”、“游牧”和“域外”等理论的试验场。 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这些号称“去中心化”的多身份的人,往往率先成为了新式集权的中心,为艺术圈源源不断地造出拙劣的“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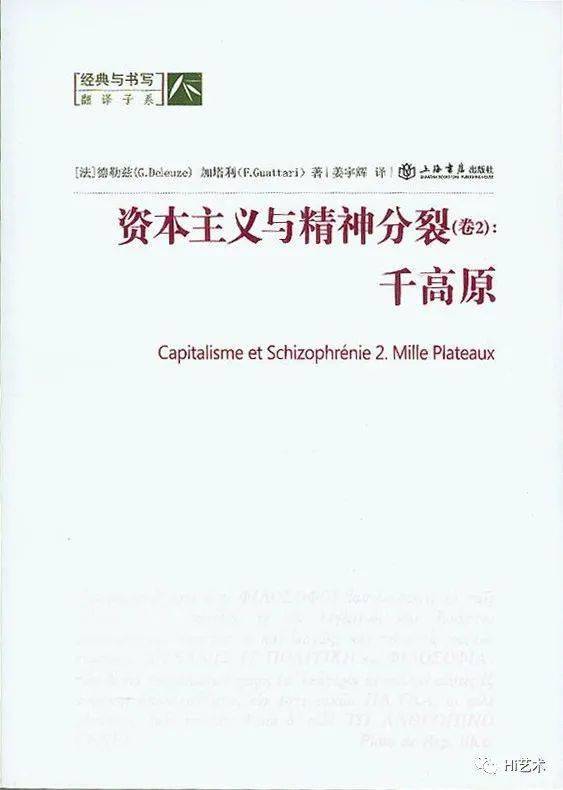
法国哲学家费利克斯·加塔利与吉尔·德勒兹合著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类(卷二)》,其中提到了著名的“块茎”理论
举一个最近在南京湖区某美术馆展览的例子,该双个展所挑选的两个国际艺术家的作品本身都是上乘之作,但是被放到这个山色掩映、景色宜人的白色建筑物里面,被直接挂在白盒子的展墙上,就好像跟艺术家本人所思考的“禁色”与内省的情感、女性主义与身体暴力没有什么关系了。没被小心处理的展墙斜度硬生生吃掉了艺术家的色彩,令一层展厅那些色彩明亮的大画看起来倒像是主人家白色衬衫上的一块“彩”渍。
斜斜的墙上,画作正朝着你尬笑。至于这样的展览到底在展示什么,我们也许可以从展签说明上一窥究竟。展签上注明的“惠允”颇为工整漂亮,几乎囊括了中国近五年来所有购买过这个外国艺术家的藏家。 馆长通过美术馆机构拿到更好的折扣,通过共同持仓同一个艺术家来建立他在艺术圈的关系网。这些借展记录所展演的“著录有序”之感,几乎可以令这个展览自行成立了。或者,不如干脆撤掉所有的画作,留下这些展签,或许可以成为汉斯?哈克(Hans Haacke)在这山中美术馆的一次特别驻留项目。


德国著名观念艺术家汉斯·哈客(b.1936)今年初在美国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现场
所有人都看到了问题,却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艺术家看艺术家的展览,只说“好”,不说“不好”;藏家看艺术家的展览,只说“好”,却不“消费”;策展人看艺术家的展览,只说“好”,看完了赶紧赴下一个饭局,再有人问还是单一个字,“好”。
这种“好上加好”的艺术圈现状,某种意义上也照应着刚刚提到的“藏家维护”。在疫情结束后的这几个月里,甚少有人还在乎生产什么艺术作品、做出什么展览,而是将心力都放在了如何活络冷淡已久的关系上。
如果你这次去上海转了几圈,不必为众人突然变得和蔼可亲而感到惊慌。因为假设你没有对应的关系可以跟他们置换,他们明年这个时候就又不认识你了。你问相熟的艺术家,他们今晚赴的什么局,他们通常总是同一个回答,“嗨,没辙,你知道的,藏家维护”。

2020上海艺术周人头攒动的盛况 摄影:董林
然而“藏家维护”,维护的实则又是什么?这大概是一种类似恋爱的关系,若即若离,明明怕被恋人抛弃,在必要场合又必须配合着恋人做出公开表演。艺术家也会疲惫,但是他们无可避免地必须要在一晚上四个饭局的窘迫之中付出移动的消耗。 到头来,新画卖没卖出去反倒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艺术家通过这种虚假的恋爱与藏家建立起来的古雅的、令人向往的“惠允”精神。


2020上海艺术周人头攒动的盛况 摄影:董林
不做知识生产的展览与藏家中心主义
当然,这种契约式精神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无奈。这种无奈体现在近期集中出现的“不做知识生产的展览”的方方面面。倘若说今年的疫情让许多人都蜷缩了起来,那么这些人这次所做的展览并未能让他们重新找到打开自己的方式。
这个情况之所以在上海更为严重,很多时候是跟长三角地区近年兴起的“藏家中心主义”趋势有关。在一个以资本分配为主导的权力分配体系当中,艺术家与藏家、评论人之间有着不言而喻的共谋关系。这让可能有效的评论反倒成了一种先抑后扬的吹捧序曲。长期把眼睛闭上数钱的人,总是以为别人亦因如是。
另一方面,前两个世纪皆已广泛讨论过的疯狂、疾病、死亡与罪恶又卷土重来,这些议题的背后勾连出的是启蒙时代之后人的主体性历史。我又忍不住翻了翻福柯(Michel Foucault),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在《主体性与真相》(1981年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课程)提及性史与疯癫史中处理主体性方式的不同时曾指出人的主体性的矛盾:“真相话语的组织是围绕着供述话语,供述的对象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们可能厌恶这一部分,我们可能自我净化去除这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和我们的所有是不可分割。”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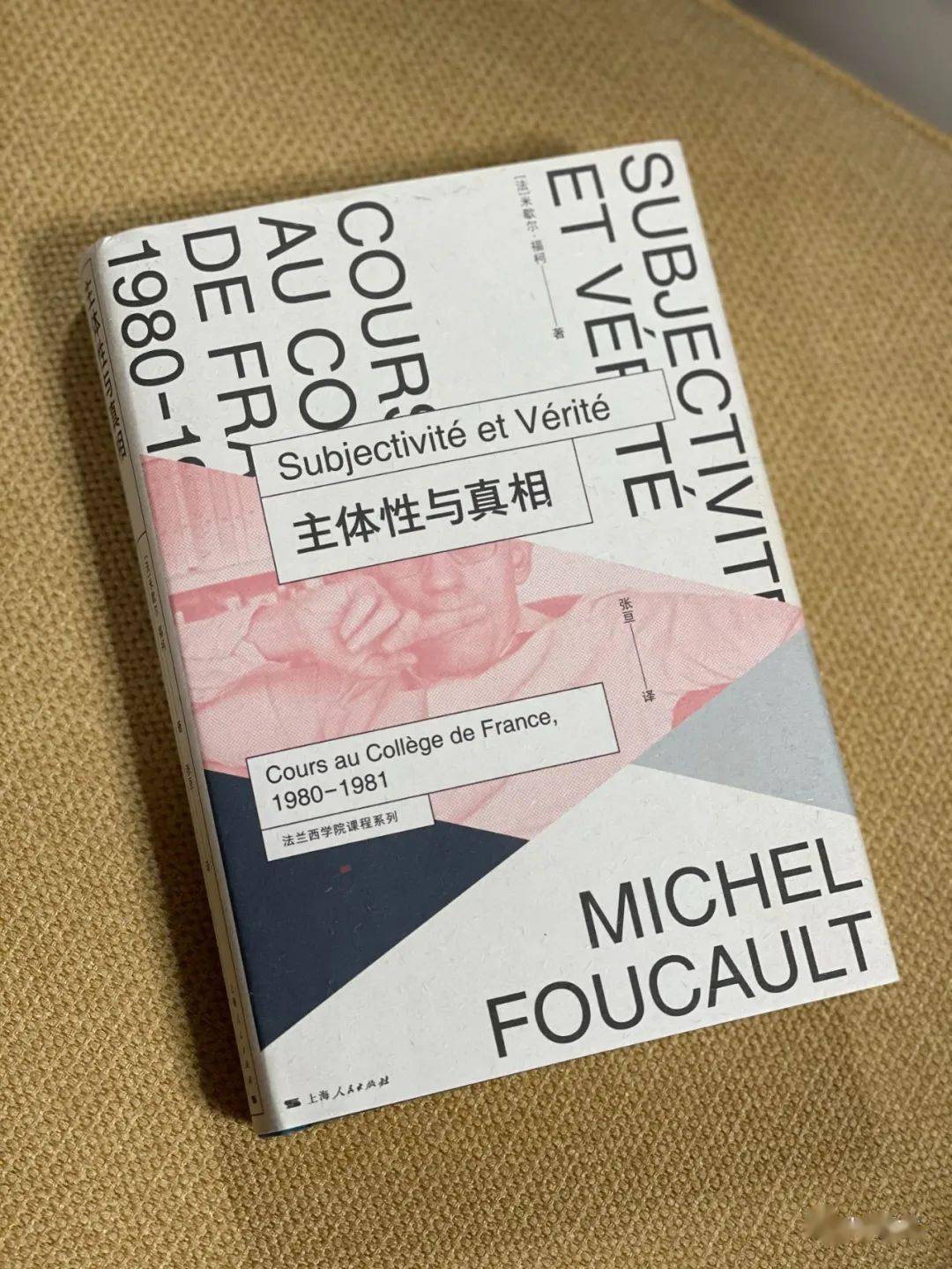
福柯在著作《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主体性与真相》中阐释过的人的主体性的矛盾,也适用于如今的当代艺术界
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提及的艺术家和美术馆自身可能也讨厌着迎合、奉承、不做生产的那一部分自己。他们在观看自己的时候,遇到的也是一种摇摆不定的感受。
可惜的是,他们近期展示的东西却无力体现他们内心的挣扎。或者还不如菲律宾国父何塞·黎萨尔(José Rizal)的小说《不许犯我》的开篇故事——一位年轻的混血主人公旅居欧洲多年之后在1880年重回故乡马尼拉,当他透过车窗观望植物园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一个倒置的望远镜的末端。 【4】
这个主人公恍然发现自己无法剥离开他脑中的欧洲花园的意象来体会现实的马尼拉花园,他的观看正在让他失去自我。
这种困境不也同样照应着“艺术家算法”与“藏家维护”,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做知识生产的展览”吗? 创作者的主体性正在通过倒置自身而远离真相,这也就意味着批评这些展览不再只是需要揭露其主体中空的问题。
沉迷于照镜子的创作者,何不借着双十一的折扣网购一面落地镜?何苦要将展览做成一个巨大的镜子,让亲朋好友八方来“照”? 这部分展览中过度阐释的词句成为空洞的文艺符号,带给人一种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神秘凝视。它们自然不提出任何良好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它们正在成为当下中国艺术圈内循环的主流——让我们再也无法如其所是地观赏“园景”,或是真切地走进一个展览。
本文由“壹伴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1】纳博科夫:“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申慧辉等译,参见《文学讲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2】纳博科夫:“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 申慧辉等译,参见《文学讲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3】米歇尔·福柯:《主体性与真相》,张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
【4】这段故事同时被汪晖引述在他2020年出版的新书中,他论述黎萨称这种双重“园景”的动因形容作“比较的幽灵”(el demonio de les comparaciones),并以此来解释一种在多重视线中同时观看他者和自我的方式,以及相应的问题。参见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07至108页。
版权与免责声明:
【声明】本文转载自其它网络媒体,版权归原网站及作者所有;本站发表之图文,均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大众鉴赏目的,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果发现有涉嫌抄袭或不良信息内容,请您告知(电话:17712620144,QQ:476944718,邮件:476944718@qq.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删除。版权所有 2000-2020 上海麟驾艺术品信息有限公司
Copyright 2000-2020 Cnarts.net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沪公网安备 31010102006431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