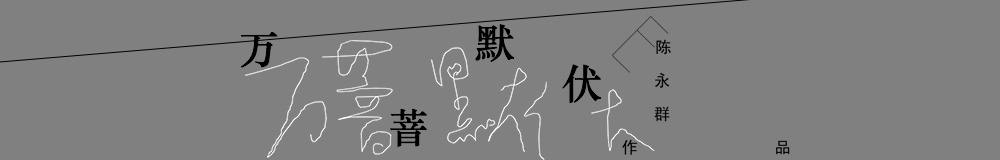“遇景”
陈永群我不知如何圆说自己,只因写字画画,是为脱离所见。无知的我,当无序显于纸:绿叶不生发,水流迟潺潺,花木休绚烂。山石林木有浑然,却也难成境。那一刻,我才知生命躯壳,可以摸着这世界,又仿佛是看“最后一眼”。
我的“景”,不是自然或萧肃情景的“用心”;只在于无设定情形下,我易于“远”去。
用纸涂涂写写违建的途径,“遇景”生成状态的机缘,如风吹翻树叶,显露叶背真相:生死悸动,有状态无自觉。悄然显现,默默消失,余下无形烟云。
无处不生的可遇之机,精神的霉菌可能会被触醒。只因自己的能量,无法引出无意识状态,情感与激情,在“我”的世界里,全然被冻结。当我个人化解于圹埌的“远景”时,就是“自我”消亡的终极理想,既不是“桃花源”,也不是归隐的“驼背”。
当身心抖去艺术史时,精神的实践,真心才显露,神魂就能回到本源:艺术此状,其果实为何等长相,实在没关系。只要有果,艺术目的其实也就完成。这是诗画的本质,也是艺术的终极意义。“无心”的游荡,是不归路,也是自己的命划过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