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三尊像的信仰转换及其图像演变
时间:2021/9/22 16:42:27 来源:佛像雕塑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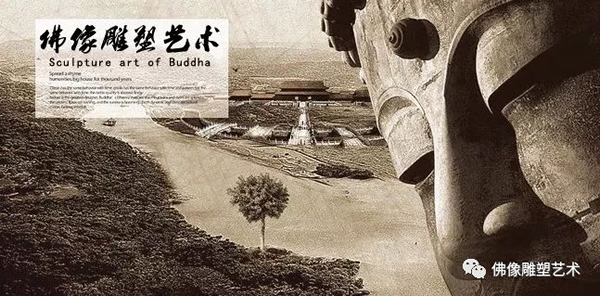
【内容提要】1、印度早期的观音三尊形式造像主要属于释迦信仰系统,其组合像式为释迦牟尼佛居中,观音与弥勒两旁胁侍;2、在佛教由印度向中国的传播中,观音三尊式造像向阿弥陀信仰系统转变,其组合像式为阿弥陀佛居中,观音与势至两旁胁侍;3、观音在两个不同信仰系统的三尊形式造像中转换的同时,其自身的图像特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源自印度的三尊形式造像,是印度佛教艺术为表现宗教崇拜主题而确立的一类特殊的“偶像式”对称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作为偶像的佛,以其高大的形体与庄严的相貌形成了视觉的中心,而侍立左右的菩萨以及其他圣众,均将观者的目光引导至中心偶像身上,从而强化了一种“向心式”的视觉效果。正因如此,三尊形式造像在印度经久不衰,且对佛教所传之处的造像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观音三尊像便是印度早期三尊形式造像中较为流行的一类。
印度早期的观音三尊像多为释迦信仰系统中释迦、观音与弥勒的组合。而在观音信仰由印度向中国的传播中,观音三尊像又向阿弥陀信仰系统中阿弥陀佛、观音与势至的组合转变。随着观音胁侍身份在两个信仰系统中的转换,其自身的图像特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印度早期的观音三尊像
有关印度观音信仰起源的时间、地点和原因,国内外学术界说法不一,未成定论。然而,从相关文献与实物资料可知,印度的观音造像最早主要是以三尊式面貌出现的,其组合样式为释迦牟尼佛居中,观音与弥勒胁侍两旁的释迦说法图像。这一研究在日本学者宫治昭的《涅磐和弥勒的图像学》一书中有集中体现。宫治昭先生曾对犍陀罗40例三尊式造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的结论是:在犍陀罗三尊形式造像中,主尊为释迦的居多,而弥勒与观音的组合则是三尊形式中二胁侍菩萨的主流。他说:“大概以释迦佛为中尊、弥勒和观音为二胁侍菩萨的犍陀罗三尊形式,在犍陀罗美术的后期大量制作。笈多朝以降,印度境内佛三尊像的基本形式得以存续并发展”。另外,发现于印度阿旃陀石窟约1-3世纪和4-6世纪的两组观音三尊式造像,也都是释迦佛居中,弥勒、观音立于两旁。还有,据《大唐西域记》载,在佛陀当年成道的地方,有一座佛寺,“外门左右各有龛室,左则观自在菩萨像,右则慈氏菩萨(即弥勒菩萨)像。白银铸成,高十余尺”。可见,在印度早期造像中,释迦牟尼佛居中,观音与弥勒两旁胁侍的三尊式说法图像不仅较为固定,而且持续时间长,流行范围广。

对于这一组合盛行的原因,李利安先生认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释迦牟尼已经灭度的期间,观音被看作是救度这个世界的主,弥勒则是未来救度这个世界的主。二者一现在,一未来,同为释迦牟尼的继承者”。宫治昭认为:“犍陀罗三尊形式的二胁侍菩萨是以梵天、婆罗门与帝释天、刹帝利两两对立的古代印度世界观为背景的,将释迦菩萨寻求菩提的形象和救济众生的形象,即‘上求菩提’和‘下化众生’这菩萨信仰根本性的两个侧面分别以弥勒菩萨和观音菩萨的尊格来体现,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不管作何解释,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印度早期的三尊式造像所反映的观音信仰主要是属于释迦信仰系统的。
二、观音三尊像信仰系统的转变
虽然释迦、观音与弥勒的三尊式说法图像在印度较为固定,而且持续时间长,流行范围广。但在宫治昭的考察中,还是有一例有铭文的三尊像表明其中尊为阿弥陀佛,左胁侍为观音。这就证明了阿弥陀信仰在印度的存在,只不过并不流行罢了。种种迹象表明,至少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我们熟知的“西方三圣”组合在印度三尊形式造像中非常少见。但这种现象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相关资料表明,在佛教初传我国的一段时间里,观音在以释迦与阿弥陀为主尊的三尊形式造像中同时并存的现象仍然是存在的。如在炳灵寺西秦建弘元年(420)的第169窟第6龛中,现存有我国最早有题名的无量寿佛三尊塑像。在这三尊像左侧绘一释迦立像,题记“释迦牟尼佛”,立像右侧绘一胁侍菩萨,题记“弥勒菩萨”,左侧为建弘元年的榜题。有趣的是,在这铺图像中,弥勒菩萨仍为释迦的胁侍,而与之对应的另一胁侍菩萨却被纪年题记所代替。而这一未被绘出的菩萨很有可能就是观音菩萨。因为,曾有学者认为,在现存炳灵寺十六国时期未有造像题名的佛三尊像中,应该有释迦三尊像,且在这一组合中,释迦与弥勒均已出现并有明确的榜题。

这一特殊的例证,说明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我国观音造像同时并存于释迦三尊与阿弥陀三尊组合之中,但其信仰的分量已经明显的偏向了后者。对此,西方三圣为塑像,释迦三尊为画像且只绘二身的情形已经做了很好的说明。另,据《历代名画记》卷五记载,东晋大雕塑家戴逵(326—392)就“曾造无量寿木像,高六丈,并菩萨”。

在敦煌莫高窟,最早有明确纪年与题记的观音画像出现在西魏大统四、五年的第285窟,此窟北壁中部通壁绘七铺说法图,其中北壁东起第一铺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式说法图,图下方正中有发愿文一方,明确表明是无量寿佛说法图。

另外,该窟东壁门南、北对称地各画一铺大型说法图,均为一佛四弟子四菩萨的组合,其中门北说法图中榜题尚依稀可见,据早期石窟记录可知,其主尊为“无量寿佛”,佛右边内侧为“无尽意菩萨”、外侧“观世音菩萨”,左边内侧“文殊师利菩萨”、外侧“大□志菩萨”。弟子四身分别题名“阿难之像供养时”、“摩诃迦叶之像”、“舍利弗之像”、“目连之像’,由此可知,这也是一铺无量寿佛说法图。这两幅图被认为是在整个北朝莫高窟仅有的两幅无量寿佛说法图。
上举三例,说明魏晋以来有明确记载与题记的观音画像,已经是阿弥陀三尊像中的主要成员了。其原因自然与阿弥陀经典在我国的翻译与阿弥陀信仰的流行是分不开的。因为,从中国的译经史来看,体现阿弥陀信仰的经典早在东汉末就已传入中土了。所以,有学者就认为,在观音的四类三尊式组合中,阿弥陀三尊组合是从汉地5世纪初开始的,其造像来源是《观无量寿经》。

三、三尊式造像中观音图像特征的演变
由于从印度到中国,观音三尊式造像的信仰系统发生了变化,所以观音的图像特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一般用来判断佛像尊格的冠饰与持物上。
在犍陀罗释迦三尊形式造像中,观音有着较为固定的图像特征,即头戴敷巾冠饰,手持华鬘与莲花(未开或开敷)。唯独前文所提一例有铭文的阿弥陀三尊像,研究这一造像的布拉夫认为其中的观音头上有化佛,可能只是一个楔形的卡子,但这并不能确定。该观音左手持未开的莲花。这就说在犍陀罗三尊式造像中,观音有化佛的图像非常少见。但在笈多时期的萨尔纳特地区则出现了一定数量头戴化佛冠的观音单尊像,同时,该地区有观音的三尊形式造像中,观音却少见化佛冠的图像特征。不过在萨尔纳特,无论是单尊还是三尊中,观音手持莲花的特征并未改变。在阿旃陀石窟的佛三尊像中,观音多与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所述图像特征相符,头前有化佛,只不过手中持物除莲花外,还有水瓶、数珠。在卡乃里,佛三尊像中观音头前除化佛外,还有多数是佛塔,手中持物还是莲花、水瓶、数珠。纳西克和卡罗拉地区的三尊像中,观音头前有化佛,手持莲花或数珠。

上述资料说明在印度贵霜王朝到笈多王朝这段时间里,观音在三尊形式造像中的图像特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则主要体现为化佛冠的出现以及持物种类的增多。化佛的出现一方面说明观音在图像特征上与阿弥陀信仰发生了关系,但另一方面又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问题:1、上述资料中所反映的佛三尊像中,与观音对应出现的另一胁侍大都被指定为弥勒菩萨。这就说,在观音三尊像的发展中,观音在图像上具有了阿弥陀系统中的特征,但与其对应出现的菩萨却不是大势至,而是释迦信仰系统中的弥勒;2、马图拉有弥勒戴化佛宝冠的高浮雕,卡乃里的观音则多头前有佛塔。这就说,一般被认为与观音相关的化佛有时出现在弥勒造像中,而与弥勒相关的佛塔则又出现在观音造像中;3、从持物来看,在犍陀罗,观音持华鬘或是带茎采下来的莲花,笈多王朝以后则是大地生长出来的莲花(开敷或未开)。但在阿旃陀和卡乃里,一直是弥勒持物的水瓶,则成为观音的持物。这些问题表明,观音三尊形式造像不仅在印度流行时间长,地域广,而且其作为胁侍菩萨成组出现的对象基本都是弥勒菩萨。而正因为这两尊菩萨关系甚为密切,所以二者的图像特征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就可能存在相互借用,相互替换的现象。也就说,至少在笈多王朝之前,印度三尊像中观音和弥勒的图像标识并不是固定的。

再来看中国早期佛教美术中观音的图像特征。正如前文所述,我国魏晋以来有明确记载与题记的观音画像,已经是阿弥陀三尊像中的主要成员,其组合对象也主要是大势至。但从图像特征上看,进入阿弥陀信仰系统的观音标识还是经历了一段由模糊到明确的演变过程。首先,还是表现在化佛冠上。从炳灵寺、莫高窟、云冈等早期的观音组合图像看,观音冠上无化佛的图像曾长期存在,在随后的发展中,有化佛与无化佛的观音图像同时并存的时间则相当长。其次,表现在观音的持物上。观音手持莲花的图像特征在中国早期的造像中继续保持,但也有一些变化。其痕迹是:4世纪的造像中,除保持持莲花的基本特征外,多持莲蕾或桃形物。自5世纪中期开始,观音图像有了突破性发展。据金申先生对山东博兴北魏太和年间十二件金铜观音造像的统计,其中有七件左手持净瓶、五件左手持披帛,而十二件造像的右手均持莲蕾。可见,净瓶与莲花作为观音的持物在此时已经广泛被应用。而北齐时代观音的持物相对减少,多以施无畏印和与愿印的形式出现。至6世纪初期,一手持杨柳,一手提瓶的“杨柳观音”像开始出现,现存较早的实例为西安历史博物馆藏萧梁普通二年(521)造像。在隋代出现的较少的几件阿弥陀整铺金铜造像中,观音的持物则有念珠(出土于河北唐县,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隋代阿弥陀三尊像)、莲蕾(1975年西安南郊东八里村出土,现藏西安博物院的隋开皇四年董钦造阿弥陀佛鎏金像)、宝瓶和经书(上世纪初出土于河北赵县,现藏于波斯顿博物馆隋开皇十三年的范氏造阿弥陀佛鎏金铜象)等。从敦煌莫高窟看,直至隋代,才在第276窟南壁说法图中,出现了头戴化佛冠,右手持柳枝,左手持净瓶的观音像。至此以后,唐代的观音三尊式造像、画像中,观音的图像特征则基本固定,即头戴化佛冠,手姿与持物则有以下几种:一、两手均结印;二、一手持净瓶,一手结印;三、一手持柳枝,一手结印;四、一手持莲花,一手结印;五、一手持净瓶,一手持杨枝;六、一手持净瓶,一手持莲花;七、一手持杨枝,一手持莲花;八、一手持杨枝,一手持插有长颈莲花的净瓶。也就说,从印度到中国,观音在三尊形式造像中的图像特征既有继承,也有变化。当观音与弥勒的图像标识在印度波罗朝得以固定下来的时候,中国的观音图像标识在约同时期的唐代也基本固定了下来(当然此后的观音造像、画像中图像标识缺失的例子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数量较少)。从此,头戴化佛冠,手持莲花、杨枝、净瓶或执手印的图像特征基本成为中国后世佛教美术中观音的“标准像”。

总之,“三尊式”作为一种经典像式,在印度及中国佛教美术史上均有着重要的地位。而释迦、观音、弥勒与阿弥陀、观音、大势至则是观音在释迦信仰系统与阿弥陀信仰系统中的“三尊式”经典组合。前文的论述为我们理清了观音在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播、发展线索中,作为胁侍菩萨的身份在释迦信仰系统与阿弥陀信仰系统中的转换,以及由此引发的其在图像特征上的诸多变化。而对观音造像的三尊形式及其图像演化的考察,不仅是从事观音图像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会将我们的视野引入更为广阔的天地。例如敦煌壁画中观音所处“说法图”对观音三尊模式的继承与发展,大型阿弥陀经变、观音经变中三尊模式的应用,以及其中观音图像特征的渊源和流变等,均将是今后有待研究与探索的,很有意思的课题。



长按关注:[佛像雕塑艺术]

版权与免责声明:
【声明】本文转载自其它网络媒体,版权归原网站及作者所有;本站发表之图文,均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大众鉴赏目的,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果发现有涉嫌抄袭或不良信息内容,请您告知(电话:17712620144,QQ:476944718,邮件:476944718@qq.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删除。- 【中国美术】 古画里的购物趣事
- 【中国美术】 齐白石别开新面画岱庙
- 【收藏知识】 鉴藏须拥“好奇心”
- 【瓷器】 瓶中淑女玉壶春
- 【中国美术】 张愚谈:本为世家真名士疑是真...
- 【其他】 筷子中隐藏的符号密码
- 【中国美术】 展览解读|王蒙与梵高,一场穿...
- 【中国美术】 诗书画的历史:从苏东坡到郑板...
- 【集邮】 书香飘逸方寸间
- 【中国美术】 丹青千载说牡丹
版权所有 2000-2020 上海麟驾艺术品信息有限公司
Copyright 2000-2020 Cnarts.net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沪公网安备 31010102006431号 |



